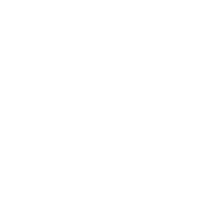【导读】从别处花钱买来孩子,再报假警称捡到弃婴,从而让买来的孩子能够顺利登记户口,让“收养”合法化。靠着这样的方式,章兴(化名)刘雁(化名)夫妇顺利将买来的女婴“合法”收养。令人错愕的是,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。

9月中下旬,根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提供的线索,澎湃新闻记者前往湖北省建始县和江苏省常熟市,以咨询落户的领养人身份,暗访两户涉嫌以“捡拾弃婴”的方式报假警,为违法收养的孩子办理落户的家庭——前者已顺利落户,后者已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案,等待出具“捡拾弃婴报案证明”,以完成整个上户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

在我国,弃婴的收养及落户,涉及公安机关、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三方,有明确的办理程序规定和收养政策。那么,违法买婴者如何通过合法渠道“洗白”襁褓婴孩身份?铤而走险的背后,又有何隐秘?澎湃新闻调查发现,购买婴儿的家庭往往存在不孕不育或者其他一些原因,遂产生了收养孩童的需求;而贩卖婴儿者,多为原生家庭无力抚养或非婚生育等多种原因。
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张善根认为,对无法生育,或失独等原因走上非法领养之路的家庭,国家相关部门需加强政策性保障和福利,但社会不该对这类所谓的 “良性违法”采取包庇或纵容的态度。

“辅警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,搞了个领养证”
章兴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人,现年36岁,个头不高,体型微胖,黝黑的圆脸总是挂着笑容。他曾外出打工,机缘巧合认识了“北漂”十多年的刘雁。刘雁来自湖北恩施州建始县,是家中长女。2017年,两人结婚后,章兴把户口迁到女方家,并跟着刘雁在亲戚的服装厂上班。疫情之后,他又搞起了社区电商。
去年8月初,有个老乡来电话,说“有一个娃娃”。想都没想,他就回复“要”。章兴和妻子算了一笔账,治疗不孕症至少要花费十万至几十万不等,还不一定能治好。现成买个孩子,只需要花不到一半的钱。这两年,夫妻俩还去过武汉和恩施两地的福利院咨询领养事宜,但都失望而归。章兴说,“恩施福利院里一个孩子都没有,登记了,也排不上。”
老乡介绍的女娃,原生家庭有些复杂:父母双方均是离异者,两人同居但还未再婚,各自还育有多名儿女。章兴称,他们不要孩子的理由很简单,就是“养不起”。章兴提供的登报公示转账记录及湖北媒体于2021年6月18日刊登的公示对方以“营养费”的名义,一开始要价6.6万元,但章兴算了算,前前后后共转账了近8万元。孩子出生第七天,他就和妻子去医院抱了回来。章兴说,为了防止孩子被要回去,他们请了当地最好的律师制定协议。厚厚一叠,像一本册子,双方签字并盖了手印。“当时我就明说,如果将来扯皮,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,大不了就一起进去吃牢饭,他们卖孩子是犯法的。”
孩子皮肤白皙,有一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,像个洋娃娃,让夫妻俩很是喜欢,但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母信息不匹配,孩子落不了户,让他们犯起愁来。“后悔死了,在医院,(孩子)父亲(一栏)本来可以写我的名字,他们都说不用,现在看来难搞了。”去年10月21日,章兴在一个讨论“送养”婴儿相关问题的微信群里“冒泡”。和群友交流中,他透露,“我派出所有熟人,说不着急,会给我搞定”,“礼都送了,都是亲戚,可以说是自己屋的人”。这两句话,引起了上官正义的注意。章兴此后向其坦言,“我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,搞了个领养证。”

孩子落户的主要依据是医学出生证明(简称出生证),可以凭司法亲子鉴定结果补办。近年来,随着对开具出生证的监管的加强,通过以“捡拾弃婴”之名报假警,并以收养弃婴的方式上户,逐渐成为“洗白”孩子身份的一种新路径——而这种“合法化”的方式,给打拐带来了更大的难度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交流,章兴逐渐放下戒备,并开始在与上官正义的微信私聊中“直播”最新进展。今年7月13日,章兴发来消息,“已经登报了,要等两个月。”9月2日,章兴又说,“我刚刚回来,今天给女儿搞户口,走正规渠道太费劲了。”
9月10日傍晚,澎湃新闻记者在建始县民政局附近见到了章兴。他刚开了80多公里山路,把负责评估收养条件的民政局工作人员送回县城。初次见面,章兴有些拘谨,但聊起给孩子上户,他逐渐打开了话匣子。他表示,“报假警”是民政局一个彭姓主任出的主意,而“派出所关系”指的是建始县公安局某派出所驻村的刘姓辅警,负责维持村里治安,三十多岁,“是刘雁的爷爷辈亲戚”。
11日上午,记者来到刘雁家,新修的两层楼房位于半山腰处,背山朝南,上下各有四个房间,门口晒着豆角和一些药材,与其他两户人家并排紧挨。章兴满头大汗赶回来,刘雁父母还留在山上忙着打理十几亩土地。推开仿红木大门,走进客厅的左侧第一个房间,刘雁独自抱着女儿偎在沙发上。她一米四十几的个头,皮肤白皙,体态丰腴。望着扑闪着大眼睛的女儿,刘雁一脸宠溺,洋溢着为人母的喜悦,“白天她爸还能抱一抱,一到晚上,就只黏着我”。孩子一岁多,她只带出门一两次,“就怕别人给我抱走了”。

章兴提供的“捡拾弃婴报案证明”、无生育证明及收养登记证章兴此前发来的“捡拾弃婴报案证明”上写着,孩子是去年8月15日凌晨2时许在自家屋后水沟处捡到的,但记者注意到,刘雁家的房子紧靠山体斜坡,坡上是一片玉米田,难以走近。“走形式来了一下。”章兴坦言,当天凌晨,他报警称“捡”到了孩子,在出警过程中,刘姓辅警“让人关了记录仪”,直接写了出警记录,盖完章就走了,“孩子丢在哪儿,都是他写的,我们只签了一个字”。出警结束后,接下来的笔录、失踪人口DNA对比等流程也“一路绿灯”。今年6月16日,派出所出具证明,证实拾到女婴“情况属实”。
送记者到村口的路上,章兴接了一通电话,他语气轻快地说,“民政局昨天来过了,星期一应该就能办好,只差这一步了”。接下来的两天,章兴带着妻子往返于县城和乡镇补齐剩余材料,办出了收养证。9月14日傍晚,章兴发来消息,“户口上好了”。匆忙见了记者一面,他便和妻子赶回长阳县。
澎湃新闻记者获取的一份报案证明显示,邻居徐老汉是事发当时的见证人。他告诉澎湃新闻,他家的房子紧挨刘雁家,事发当时,他并未亲眼见到女婴被弃在刘家门前,直到次日刘家亲属抱着孩子到其家中借婴儿衣服,才被告知孩子是凌晨捡到的。孩子被丢在哪儿?他也说不清,“大概是丢在家门前吧。”他还表示,女婴被弃前,就已经在刘家住上了。
9月15日,澎湃新闻记者来到建始县民政局,找到了章兴多次提到的彭姓主任,他是儿童及养老福利科的负责人。建始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一开始,记者以当地人的身份,询问如何将领养来的孩子合法化,他表示,“违反法律法规,涉及到买卖关系都不行。”聊了一会儿,见记者似乎有难言之隐,他示意可以去屋外谈。走到屋外的开阔处,彭主任点上烟,开门见山说道,“把你们的情况如实和我说”。当记者表示有一个买来的孩子,无法办理出生医学证明,能否通过“捡拾弃婴”的方式报假警上户,他犹豫了一下,说:“捡拾(的方式)很难,但你们能把那边弄好的话,也可以。”
他所说的“那边”,指的是基层公安部门。“孩子丢在哪儿,就找对应辖区派出所负责出警的人。”彭主任解释道,处理弃婴的收养问题,民政部门以公安机关的核查为准,在调取报案记录、失踪人口DNA对比结果等资料后,进入登报公示流程,“至少公示2个月”,接下来,核查收养人的犯罪记录、家庭收入情况、房产证明等情况,核查是否符合收养条件。

根据我国《收养法》要求,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:无子女;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;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;年满三十周岁。章兴夫妇均满足以上条件。当记者追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落户,彭主任表示,“只能报警,没有其他路了。”章兴此前提到,从报案开始到上完户口,孩子都一直在家里。但根据2013年发布的《民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安部 司法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》,公告期满后,仍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,需经主管民政部门审批后,办理正式进入儿童福利机构的手续。
对此,彭主任解释,疫情期间,福利机构内部采取封闭式管理,孩子均由符合收养条件的报案家庭暂时寄养。建始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院长詹顺国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,福利机构以民政局审核后的材料为准,不单独做调研评估,“只负责盖章”,收养登记、评估及发证,都由民政局彭主任一人负责。对于以“捡拾弃婴”的方式报假警上户这一问题,他回复,“只要程序合法,符合收养条件,就可以办理”。
村里张贴的“民辅警联系牌”詹院长还表示,目前当地有数十户家庭登记领养,但一般而言,采取“谁捡到、谁领养”的方式处理,“自己找(孩子的)来源”。他直言,不少家庭是因为孩子上不了户口,才办理收养证,“有些孩子已经养了好几年了”。也就是说,在弃婴的收养及上户所涉及到的三方机构中,公安机关是第一关,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关。根据章兴提供的信息及村里张贴的“民辅警联系牌”,记者拨通了刘姓民警的电话,但他否认与刘家相识,也不愿意作进一步沟通。

“宝宝在这样的原生家庭,实在太惨了”
去年12月,张芦依和上官正义在一个名为“缘分到了”的送养微信群里相识,彼时,她正急切地寻找送养人。张芦依今年8月中旬,张芦依传来了好消息,说领到了一个三个多月大的女宝。为了给孩子上户,她也准备以“捡拾弃婴”的方式报假警,“我们跟派出所说好了,等那个接警员值班。”9月1日,她又发来消息,“昨天刚去派出所报案了,等出证明。”9月16日,澎湃新闻记者在常熟市一餐厅见到了张芦依。说起领养孩子的经历,她眉头皱成一团,开始大倒苦水。
她现年32岁,和丈夫都从事会计行业,经相亲介绍后,2014年结婚。婚后,一直与男方父母住在一起。二人世界虽潇洒,但在长辈的心里,没有孩子,始终是一个心结。张芦依说,每年过年,双方亲戚围在一起吃饭,都要提起孩子的事。有一天,张芦依母亲不经意说了一句,“我都怕到你家吃饭了”,深深刺痛了她。“关键又不是我们不愿意生了,也是没办法啊,反正外人是不会理解的。”她的话语里满是无奈。
她想过做试管,但怕风险太高,也想过去福利院登记,但身边的朋友亲戚都劝她放弃,“福利院里绝大多数都是有缺陷的孩子,没有人会白送健康的宝宝进福利院,确定不要就托人找买家。”2016年,经介绍,张芦依认识了一位未婚先孕的高中生。一开始,双方谈好了价钱,但等张芦依夫妇赶到了医院,对方突然变卦,说要把孩子送给自家亲戚。“卖孩子的人会同时找很多下家,估计有人出了更高的价格吧。”对第一次失败,她始终有些耿耿于怀。

接下来的几年,托亲戚、朋友帮忙留意,搭上一些送养人,但领养之路始终不顺利。“每次问有没有,都说有有有,但后来都不了了之。”张芦依说,有个孕期9个多月的产妇,开始谈得好端端的,后来以感冒为借口,说把孩子打掉了。“谁信?现在没有孩子(的家庭)很多,孩子很抢手,就看谁出钱多呗。”
今年6月,张芦依的姑妈还在饭桌上提醒她,“有没有熟人,赶紧去领一个,没有孩子是不行的。”8月初,在一次喜宴上,张芦依婆婆的朋友提到有个女娃。当时,这个孩子已经三个多月大了。为了避免再被对方放鸽子,经两方中间人沟通后,张芦依和丈夫商量,第二天就把孩子抱回来。本来双方说好的是8万元,但接走的前一晚8点多,中间人通知她,“带好9万,孩子接走。”当天清晨7点多,张芦依和丈夫一行4人来到了送养人提供的地址,眼前的场景让她有些吃惊。
张芦依称,这是位于张家港的一个工厂宿舍,一家四口挤在不到5个平方的小房间里,除了一张床,几乎没有别的家具。孩子刚刚洗完澡,躺在床上。旁边只有一个奶瓶、一个温水壶,还有一罐奶粉,“没见过的牌子”。张芦依说,孩子的亲生父母均是外来打工人员,三十多岁。两人各自在老家有孩子,再婚后育有两个女儿,一个三岁多,张芦依领养的是老二。给完现金,张芦依让婆婆赶紧把孩子抱走。孩子的母亲本想收拾两件衣服让她带走,回头看到孩子不见了,只是淡淡说了句,“已经走啦”,就忙活别的事情去了。